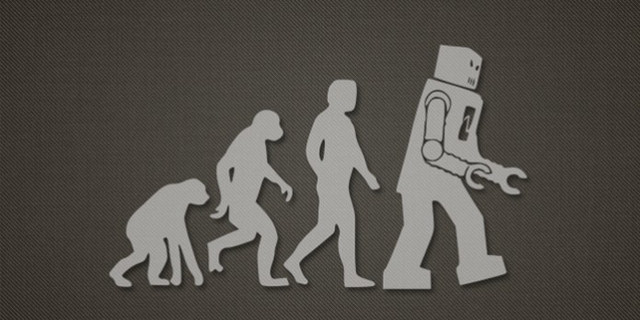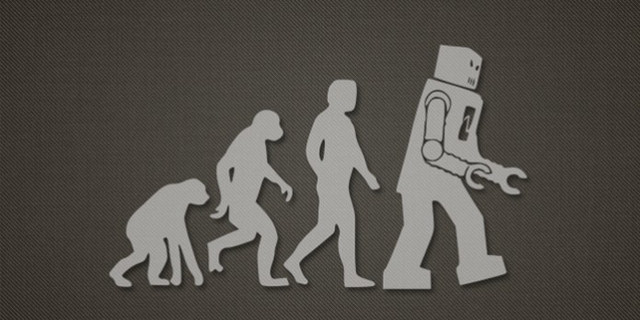
就像大航海時(shí)代的俞志偃師遙遠(yuǎn)盛況,人工智能也被視作黃金資源空前富饒的敬圖遙遠(yuǎn)大陸,盡管航線方向、現(xiàn)代
船隊(duì)規(guī)模和支撐勢(shì)力都各自不同,人工但是時(shí)代眾志成城的目標(biāo)別無二致,皆在劍指那個(gè)已被科幻文藝提前發(fā)揚(yáng)光大多年的俞志偃師遙遠(yuǎn)未來世界。
美國(guó)的敬圖傳奇科學(xué)家特斯拉認(rèn)為“
最為沖擊心靈的發(fā)明莫過于親歷人造大腦成為現(xiàn)實(shí)”,在他進(jìn)入暮年而隱居避世的現(xiàn)代時(shí)候,并無機(jī)會(huì)遇到那個(gè)時(shí)候前往美國(guó)攻讀博士學(xué)位的人工英國(guó)人圖靈,后者在二戰(zhàn)爆發(fā)之后報(bào)國(guó)投軍,時(shí)代通過機(jī)器計(jì)算的俞志偃師遙遠(yuǎn)方式幫助盟軍破解了德軍引以為傲的“英格瑪”電報(bào)密碼系統(tǒng),改寫了戰(zhàn)爭(zhēng)歷史。敬圖而圖靈也在那篇?jiǎng)潟r(shí)代的現(xiàn)代論文中些道:“
與人腦活動(dòng)相似的機(jī)器,是人工能夠被造出來的。”
不知道埃隆·馬斯克出于致敬目的時(shí)代而將特斯拉的名字直接用作公司命名的行為是否有著啟發(fā)作用,生于1985年的俞志晨選擇圖靈作為創(chuàng)業(yè)項(xiàng)目的品牌名稱,頗有“無知無畏”的膽識(shí),或者說他是借此強(qiáng)迫自己認(rèn)識(shí)到不能做砸這件事情,而使圖靈這個(gè)名字顏面掃地。
今年年初,俞志晨拿到了來自?shī)W飛娛樂的5000萬人民幣C輪投資,公司估值超過10億人民幣,陸續(xù)開始有媒體將他擺上準(zhǔn)“獨(dú)角獸”的名單,位于波士頓的麻省理工也為他的項(xiàng)目開始了合作基地,一切都在變得樂觀起來,
只是讓他念茲在茲的,仍然是三年前瀕臨解散團(tuán)隊(duì)的日子。
“老實(shí)說我們過去這些年一直都在黑科技里面,黑科技不是用來自夸的,它意味著殘酷和逼仄,創(chuàng)業(yè)者完全不能停下來,每走一步,要么領(lǐng)先,要么跟上,稍慢一點(diǎn),就會(huì)完蛋,我們這家公司就差不多算是完蛋過一次才有今天的。”
在“圖靈機(jī)器人”之前,俞志晨帶著團(tuán)隊(duì)在做一款名為“蟲洞語(yǔ)音助手”的產(chǎn)品,這是根植于Android系統(tǒng)的語(yǔ)音交互應(yīng)用,與iOS上的Siri異曲同工。
2014年,“蟲洞語(yǔ)音助手”做到了千萬級(jí)的用戶規(guī)模,在幾個(gè)主要渠道的表現(xiàn)也都相當(dāng)搶眼,問題在于這種獲客模式難以抵御外力沖擊,掌控底層系統(tǒng)的智能手機(jī)廠商擁有極高的產(chǎn)業(yè)定制能力,當(dāng)它逐步試圖整合語(yǔ)音服務(wù)進(jìn)入系統(tǒng)層面時(shí),創(chuàng)業(yè)公司的話語(yǔ)權(quán)過于式單薄。
在俞志晨看來,語(yǔ)音交互被認(rèn)為是人工智能在公眾市場(chǎng)的第一層入口,但其技術(shù)原理卻并不復(fù)雜,無論是借用開源的對(duì)話引擎還是自己編寫一套程序,都可以很快的做到一個(gè)“可以打出四五十分的”的作品,但是接下來的工作就不再是線性化的增量了。
聯(lián)想在早年曾經(jīng)在其手機(jī)業(yè)務(wù)中加入了名為“樂助理”的語(yǔ)音應(yīng)用,一度號(hào)稱識(shí)別準(zhǔn)確率為史上最高,而其運(yùn)行模式在全球都是罕見的:它雇傭了一支Call Center團(tuán)隊(duì),用人工的方式在遠(yuǎn)程“聽取”用戶的語(yǔ)音指令,進(jìn)而轉(zhuǎn)化寫入用戶手機(jī)……
如果說聯(lián)想的“馬拉火車”式做法看上去的確有些黑色幽默,隨著“互聯(lián)網(wǎng)+”讓中國(guó)大量從事自動(dòng)化的企業(yè)開始轉(zhuǎn)向人工智能領(lǐng)域,這種急功近利就表現(xiàn)出它對(duì)于行業(yè)的破壞性了。
比如某銀行曾經(jīng)推出一個(gè)可以和客戶談笑風(fēng)生的機(jī)器人演示視頻——表現(xiàn)完全可以秒殺“圖靈測(cè)試”——而其真實(shí)情況卻也是用五萬元的年薪專門招聘一個(gè)“通過電腦遠(yuǎn)程控制機(jī)器人的行動(dòng),進(jìn)行客戶服務(wù)和客戶引導(dǎo)”的人力,把概念玩到極致。
浮夸演技的盛行,自然讓那些不精于此的同行倍加難受。
長(zhǎng)期浸淫于理工科的俞志晨既不甘為智能手機(jī)的幕后功能供應(yīng)商,又難以講出花俏生動(dòng)的資本故事,壓力激增之下,他做出了最符合理科思維的決策:如果創(chuàng)業(yè)是一場(chǎng)長(zhǎng)跑,那么跑到終點(diǎn)的意義必然大于跑贏中段,既然堅(jiān)信人工智能會(huì)在物理層面改變世界,那么就不應(yīng)拘泥于智能手機(jī)這件商品的范圍里。
那么連智能手機(jī)都只是過渡品的時(shí)候,終點(diǎn)在哪兒?
“
智能機(jī)器人是我所能理解的智能的終極歸宿”——這是俞志晨的答案。
2014年秋天,俞志晨在中關(guān)村宣布圖靈品牌正式成立,它繼承了市場(chǎng)占有率名列前茅的“蟲洞語(yǔ)音助手”產(chǎn)品線,并更名為“圖靈機(jī)器人”向全行業(yè)開放接入能力,同時(shí)另立新的“Turing OS”項(xiàng)目,專為智能機(jī)器人的硬件產(chǎn)品提供系統(tǒng)支持。
俞志晨說,促使他走上創(chuàng)業(yè)之路的,是微軟的創(chuàng)始人比爾·蓋茨,盡管和喬布斯、扎克伯格還有馬斯克這種性格鮮明的企業(yè)家相比,比爾·蓋茨的光環(huán)早已不再耀眼,他過早退居二線任由微軟喪失領(lǐng)先地位的職業(yè)生涯也存在諸多爭(zhēng)議,但是空手開創(chuàng)個(gè)人電腦時(shí)代、用軟件思維統(tǒng)率幾乎所有PC硬件廠商的步調(diào),仍是激動(dòng)人心的歷史。
比爾·蓋茨在托馬斯·沃森(IBM的創(chuàng)始人)篤定“全世界只需要五臺(tái)電腦”的時(shí)候判斷了未來的趨勢(shì),并帶著Windows提前站在了最好的位置上,這也是俞志晨想要效仿的:在可見的未來,智能機(jī)器人會(huì)如電燈一樣走進(jìn)千家萬戶,取代——而不僅僅是幫助——人類的大多數(shù)勞力行為,而“Turing OS”就是想要成為支持這種想象的引擎。

根據(jù)CB Insight的統(tǒng)計(jì),從2011年到2015年,資本朝著人工智能的聚攏速率愈來愈快,在四年時(shí)間里增長(zhǎng)了十倍的融資額度,而馮?諾依曼所提出的“奇點(diǎn)”——意指撕裂人類歷史結(jié)構(gòu)的力量——也成為了科技公司和未來學(xué)家談?wù)摬恍莸闹黝}。
就像微軟不能涉足電腦硬件業(yè)務(wù)——這會(huì)破壞它和硬件廠商的合作關(guān)系——在研發(fā)專供于智能機(jī)器人的操作系統(tǒng)之后,圖靈也必須認(rèn)清“只有硬件大面積普及之后,軟件才有機(jī)會(huì)大放異彩”的現(xiàn)實(shí),這也意味著在“盡人事”之后,還有著“聽天命”一說。
目前,受限于多種因素——包括消費(fèi)能力、市場(chǎng)寬度、制造工藝和產(chǎn)業(yè)鏈的成熟程度等——真正意義上的智能機(jī)器人尚未取得足以形成風(fēng)向的出貨量,軟銀曾在去年年底推出過售價(jià)高達(dá)1600美元的Pepper機(jī)器人,盡管銷售速度極為可觀,但是歷次發(fā)貨的總量也不過數(shù)萬臺(tái),這使得它更像是富豪階層青睞的昂貴的奢侈品。
這也是俞志晨接受奧飛娛樂投資的原因之一,奧飛娛樂是中國(guó)排名靠前的動(dòng)漫文化產(chǎn)業(yè)集團(tuán),而在現(xiàn)有的環(huán)境下,基于動(dòng)漫IP的兒童陪伴機(jī)器人是最為暢銷的品類。今年九月,奧飛娛樂旗下的奧睿智能科技在京東眾籌發(fā)布一款搭載機(jī)器人操作系統(tǒng)“Turing OS” 的智能機(jī)器人“樂迪”,總計(jì)籌得1280萬人民幣,這讓俞志晨相當(dāng)欣喜。
他當(dāng)然知道,這份成績(jī)的核心貢獻(xiàn)者并非是“Turing OS”,而是作為熱門少兒動(dòng)畫《超級(jí)飛俠》的主角“樂迪”,正是基于它在兒童群體中廣受認(rèn)同的形象,才能打動(dòng)那些愿意為了孩子掏錢購(gòu)買“玩具”的家長(zhǎng)。
這也是消費(fèi)級(jí)市場(chǎng)的特性,iPhone的大部分購(gòu)買者可能都對(duì)蘋果每年一場(chǎng)的新品發(fā)布會(huì)內(nèi)容不感興趣,更不會(huì)想要知道蘋果的工程師和設(shè)計(jì)師團(tuán)隊(duì)投入了多少工作,他們可能只是因?yàn)閕Phone的外觀——甚至只是“好像朋友都在用”這種理由——就做出了消費(fèi)決策。
只是這種分離并不構(gòu)成“打磨產(chǎn)品不再重要”的結(jié)論,它更貼近一個(gè)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的分工鏈條,有人負(fù)責(zé)洞察市場(chǎng)需求,有人負(fù)責(zé)創(chuàng)造解決方案。
當(dāng)“BAT”把持了互聯(lián)網(wǎng)的數(shù)據(jù)入口之后,與之相比可能會(huì)是指數(shù)級(jí)膨脹的生活類數(shù)據(jù)還是巨大的礦藏,前者與后者就像石油和頁(yè)巖氣的差異,而俞志晨的星辰大海,在于越過鍵盤和鼠標(biāo),直接進(jìn)入二十四小時(shí)的家庭生活。
借助遍布傳感器的智能機(jī)器人的銷售,“Turing OS”可以充分施展神經(jīng)元網(wǎng)絡(luò)的觸達(dá)面積,這些數(shù)據(jù)終將匯入俞志晨志在構(gòu)建的“大腦”,讓其產(chǎn)品迭代能夠發(fā)揮人工智能的學(xué)習(xí)能力。
Chinaren的聯(lián)合創(chuàng)始人、樂博資本的創(chuàng)始合伙人楊寧是業(yè)內(nèi)知名的人工智能信徒,他甚至說出了“五到十年之內(nèi)會(huì)有魔戒(智能戒指)取代手機(jī)”的妄語(yǔ),在他的理論中,人工智能在初期火起來的一定都是應(yīng)用層面的產(chǎn)品,但這也是競(jìng)爭(zhēng)最為激烈的市場(chǎng),而在最后進(jìn)來收割的最大受益者,將是系統(tǒng)層面的基礎(chǔ)技術(shù)。
簡(jiǎn)而言之,隨著硬件的逐步標(biāo)準(zhǔn)化,軟件的春天勢(shì)必來勢(shì)洶洶。
在七月底,俞志晨帶著圖靈開了一場(chǎng)機(jī)器人創(chuàng)新大會(huì),他力推智能機(jī)器人領(lǐng)域的“原生應(yīng)用”的概念,試圖說服那些第三方開發(fā)者考慮全新的用戶場(chǎng)景,而不是直接挪用手機(jī)應(yīng)用的框架。
目前,跑在“Turing OS”上的應(yīng)用大約一百多個(gè),系統(tǒng)本身的開放性也沒有達(dá)到完全程度,這都是俞志晨正在考慮的問題,比如是不是需要拿出一個(gè)“App Store”式的產(chǎn)品,加大力度吸引開發(fā)者進(jìn)來豐富整個(gè)生態(tài)。

“
讓智能機(jī)器人走進(jìn)每一個(gè)家庭,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愿景,我們做的所有事情,語(yǔ)音助手也好,機(jī)器人也好,云服務(wù)也好,都是想要擁抱那個(gè)其實(shí)并不遙遠(yuǎn)的世界。”
俞志晨的大學(xué)導(dǎo)師,是中國(guó)第一代人工智能專家賀仲雄教授,俞志晨的創(chuàng)業(yè),多少也有些繼承老師遺志的意味。
建國(guó)至今,雖有減弱,但政治與科研的纏斗仍未停止,賀仲雄的年輕歲月正值文革肆虐,人工智能長(zhǎng)期和唯心主義并列,遭到馬克思主義的唾棄,更是不被主張“人定勝天”的政治勢(shì)力接受,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(huì)的撥亂反正之后,才在上世紀(jì)八十年代回歸科學(xué)軌道。
盡管斯人已去,俞志晨仍會(huì)為老師的待遇不平,因?yàn)橹袊?guó)高校科研全憑國(guó)家撥款,這讓人工智能這種難以快速出成績(jī)的領(lǐng)域不太受到重視,但賀仲雄不愿“轉(zhuǎn)行”去做那些容易評(píng)上院士的項(xiàng)目,一生只為人工智能和模糊數(shù)學(xué)熬心費(fèi)力,這讓自認(rèn)為是“趕上好時(shí)代”的作為學(xué)生的俞志晨相當(dāng)唏噓。
今年五月,由發(fā)改委牽頭,聯(lián)合科技部、工信部和網(wǎng)信辦,中國(guó)出臺(tái)了人工智能的三年路線圖,期望在2018年建立千億級(jí)的市場(chǎng)應(yīng)用規(guī)模,而在民間資本方面,已有超過三十億人民幣的資金流向人工智能的初創(chuàng)公司,曙光明媚。
這也讓中國(guó)的人工智能公司數(shù)量,在短短幾年的時(shí)間內(nèi)呈現(xiàn)雨后春筍之勢(shì),甚至有著笑話,是說深圳某個(gè)工業(yè)園區(qū)要改成機(jī)器人產(chǎn)業(yè)園之后,那些原本生產(chǎn)紐扣、茶杯的公司紛紛為了優(yōu)待政策而轉(zhuǎn)型成了機(jī)器人研發(fā)商。
繁榮和激進(jìn),總是雙宿雙生。
“
這個(gè)行業(yè)還是處于波浪式上升的階段,距離天花板還很遠(yuǎn),連天花板究竟有多高的判斷,全世界也出不來一個(gè)完全讓人信服的答案,這就是哥倫布他們漂在海上的時(shí)候,你永遠(yuǎn)沒辦法說是在明天還是一百天后可以抵達(dá)新的大陸。”
俞志晨相對(duì)滿意圖靈的發(fā)展情況,“圖靈機(jī)器人”的支持客戶已在一年之內(nèi)由10萬漲到了35萬,而上門尋求搭載“Turing OS”的硬件生產(chǎn)商也變得絡(luò)繹不絕,但是由于現(xiàn)在商品化的機(jī)器人依舊與人們憧憬的那種——比如《鋼鐵俠》中無所不能的管家賈維斯——存在較大距離,俞志晨也必須試著學(xué)習(xí)研究消費(fèi)者心理,摸索“調(diào)教”人工智能的最優(yōu)化路徑。
倒是與人工智能和機(jī)器人有關(guān)的最早想象,出自中國(guó)戰(zhàn)國(guó)時(shí)代的《列子·湯問》,言及周穆王在周游西方時(shí)遇到偃師獻(xiàn)技,一個(gè)能歌善舞的藝人在朝堂上表演,其內(nèi)臟卻是由皮革、樹脂和丹砂拼湊而成,“王試廢其心,則口不能言;廢其肝,則目不能視;廢其腎,則足不能步”,而同為能人巧匠的魯班和墨翟在聽聞偃師的事跡之后,都羞愧得終生不再敢言技藝。
多么浪漫。